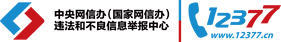晚饭后,我常会到河堤上散步。清溪河畔,凉风习习,我走在河堤上,望着潺潺的河水,听着“汩汩”的水声,总想着,在那段湍急的河水里,这时候应该有一个“方”,这“方”明儿一早一定能接很多很多的鱼儿吧!想着想着,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家乡,又回到了我的童年。
我的家乡在店垭镇垭子口村,这里被群山环抱,东边与南漳县交界。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,河水不大,清激的河水,沿着山脚悄悄地流淌着,不声不响地穿山而过,注入沮水,融入峡口水库。河水时而奔腾,时而平静,就像一曲舒缓的曲子一年四季凑响在家乡的山边、田野、天空。那两岸长满青草的弯弯的小河,曾经是我的乐园。
春末夏初,山色葱葱,河水潺潺。那时候,我们除了上学外,还要一早一晚地放牛。
每天傍晚放学回家,我们几个放牛娃便不约而同地将牛赶到河里,牛儿很习惯地也是迫不及待地奔向河潭里洗澡去了。我们一群放牛娃则在河边撒着欢地玩耍。我们有时脱光了衣服也跳进水潭里,泥鳅一般在河水里蹿来钻去的嬉戏打闹,有时在河岸边那如茵的草地上打滚摔跤,最多的时候,则是在河里逮鱼摸虾。
那年月,小河里的鱼虾特别多,什么白鲃子、红翅膀(就是长着红色鱼鳍的公白鲃子,我们有时也叫它“桃花”)、沙股溜儿、泥鳅、鳝鱼、鲫鱼、鲤鱼、麦惠子等等,还有团鱼、乌龟、河虾等,其中白鲃子和红翅膀最多。当然,我们逮鱼的法子也很多。大人们多用撒网,我们放牛娃的法子就简单实用多了:有徒手在石缝里摸鱼的,有用锤子砸的(实际是砸水中的石头把石缝里的鱼给震出来),有用柳树叶浆汁毒的,还有一种简单省事的方法,那就是捡方。
这捡方,须是春未夏初才好。这时节,河水不大不小,徐徐缓缓,清澈而暖和。倘若在冬季呢,河水又冷又小,鱼也少;仲夏时节呢,则水又太大了,此时捡方难度大,也逮不到鱼。
再就是要挑选好的河段。这捡方的河段,须是河水湍急且河床较窄的地方才好。我们一般会在这样的河段,顺着水流的方向,将河水中的泥沙扒出一个连着两岸的倒八字,让河水从倒八字的窄口流出,然后在倒八字的窄口处,利用落差,用方正的石块垒成一个约一尺宽的小“瀑布”,在“瀑布”的落水处掏出一水窝,如此,一个捕鱼的“方”便初具雏形了,它就像一个平面的漏斗。剩下的就是逐步修理完善的活儿了,比如要把方里的大一点石块清理干净,不给鱼儿逗留或躲藏的空间。再比如,要把方的堤坝(就是倒八字的两撇吧)修筑牢固,得用细一点的沙土填上去,让其尽量地不漏水,不漏鱼儿。方口更要筑得紧实,必要时还须掺些水草和泥巴用脚踩实才行的。当然,这些活儿对我们这些放牛娃来讲,它就是小莱一碟儿,根本不用什么工具,大伙儿光着屁股,你捡石头,我刨沙,一袋烟的功夫便大功告成。
这方捡成了,怎么逮鱼呢?
其实,这方逮鱼的秘密就在它的“瀑布口”。那时候,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鱼篓子,这鱼篓基本上是方口接鱼专用的,它有一个椭圆形的口,一尺来长,鱼篓的大小和长短正适合放在方口的下方,能让“瀑布”直接流进鱼篓里。黑夜里,在觅食到方坝里的鱼儿会困湍急的水流不知不觉地顺流而下,糊里糊涂地流进鱼篓了。这样逮鱼是不是特简单!也正因为如此,所以在这时节,小河里每隔一段距离,在那响水的河段都会见到这样一个方。
我们一般是谁捡的方谁接鱼,要是大伙儿合作捡的方呢,我们就一人一晚轮流着去接鱼。不是自己捡的方,一般是没人去接的,当然,就更没人去偷了。也有人路过时会把鱼篓捞出来看看,然后原封不动地放回原处,也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。
在初夏的晚上,乘着落日的余辉,我们哥儿几个便挎上鱼篓,拿上手电简,像城里人散步似的,一路说笑着来到河边。我们先在方的“瀑布”口安放好鱼篓,然后再搬个大石块把鱼篓从下边给靠压着,以免它被水冲走了,最后还不忘扯点水草丢在鱼篓里,这也是为了防止进了篓子的鱼再飞出来。眨眼功夫,万事俱备,就只等收鱼了。
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,清凉的河风有些醉人。河边很寂静,除了潺潺的流水声,还有布谷鸟那清脆婉转的歌声――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,不知怎的,这歌声总听不够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不管是在家乡还是异地。等月儿爬上山顶挂上树梢时,我们便会在河堤上坐会儿玩会儿,小声地说着话,生怕惊着了方里夜游的小鱼儿。有时也忍不住去方口前看看,忍不住伸手去鱼篓里摸上一摸,看看有没有惊喜。当然,我们更愿意把这惊喜留到第二天清晨。
有的时候,我们在方口安放好鱼篓后,还会去“撮火鱼”。“撮火鱼”须用上火把、撮筐,火把和撮筐都是用竹篾做的;须在河水平缓的水滩里才行,撮的鱼也非“火鱼”。这时节,河水不大,清澈暖和,有些鱼儿一到晚上便呆在沙窝里,见了火光,更是一动不动地傻呆着。这时,你便可以用撮筐悄悄地从下水处由下而上地靠近鱼儿,慢慢地将泥沙和鱼一起撮进筐里,再轻轻地抬高撮筐口迅速带出水面,鱼儿便稀里糊涂地被装进鱼篓了。我们管这种利用火把照着逮鱼的法子叫“撮火鱼”。撮鱼的多半是大一点儿的兄长,因为速度的掌握很重要,我呢多半是打火把的,只能耐心地听着兄长小声地指挥着“高一点”“再低点儿”“往前一点儿,好了,别动!”唉!谁让你技艺不高呢,打下手只能这样!不过也挺乐意的。运气好的时候,收获也是不错的,只是泥鳅居多,也有鲫鱼、麦惠子、河虾等,因为其他的鱼是很少扎窝的。
漆黑的夏夜,小河里上上下下,常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撮火鱼。那闪闪烁烁的火光,像飞舞的萤火虫,也有点像闪烁的星星。
第二天清晨,我们便很早起床,兴奋地直奔河里的方口,掀开压在鱼篓边上的石头,迅速地提起鱼篓,追不及待地捞出放在鱼篓里的水草,抖一抖篓子,看看有没有惊喜。当然,这惊喜有大有小,少的时候,做个下酒莱是没问题的;这多的时候,也有小半篓二三斤的样子。一般雨天前后,收获要多一点,有时还能接着团鱼之类的呢。不过,偶尔也惊吓等着你。有一回,我哥就发现鱼篓里装着一条蛇,当时吓得连鱼篓都扔了,好几天都没敢去方口接鱼。
在那个年代,我们一大家子常常一年到头很少吃上肉,但我们却能三天两头地吃上鱼,而且我母亲还是烹鱼的高手,每每逮着鱼了,不论鱼多鱼少,还是鱼小鱼大,母亲都会及时地做出来,香喷喷地端上桌,我们都特别爱吃,就连煎鱼的佐料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。直到现在,我每次回到老家,母亲都要亲手做一道我们爱吃的鱼。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,门前的小河似乎也变老了。每次回去,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到小河边走走看看。只是,那河边啃草的牛群不见了,那光着屁股戏水打闹的放牛娃也没影了,还有那如茵的草地也消失了。潺潺地流水变成了涓涓细流,溪水里别说鱼了,就连小虾的影子也难得一见。当年捡方的河滩也变了模样,有的长满了荆棘,有的变成了柳林。唉!小河不仅老了,脾气也变坏了,她时而干涸沉寂,时而又咆哮愤怒,变得让人陌生,变得让我敬而远之。
现如今,二哥的大孙女梦梦也都上幼儿园了。梦梦说话时总带着笑脸,嘴巴也很甜,挺招人喜爱的,也很粘人。有时我到河边去走走,她就像小尾巴一样地跟着我,我便给她讲这小河里的故事,她呢,常会仰起那稚气十足的脸问我“幺爷,那水牛长啥样呀?”“幺爷,那‘方’在哪儿呀?”“幺爷,这水里咋就没见鱼呢?”唉!我有些羞愧似的无言以对。当然,像她们这代人,甚至包括她的父辈,是不会知道何为“方”,啥叫“撮火鱼”的。我不知道,这捡方、撮火鱼算不算“传统技艺”,能不能被“申遗”,我能做的,只是悄悄地无奈地把她们装入我的行囊里,也装进我的梦里。
山色葱葱,河水潺潺,我仿佛又看见了一群光着屁股的放牛娃,在门前的小河里,有的搬石块,有的刨沙土,正嘻嘻哈哈地维修着那被水牛踏坏的方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