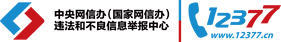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”。印象中,江南的荷是小荷,梗小,叶小,花小,像江南的女子,纤细而斯文。
家乡的荷,梗粗壮,叶撑的也开,大的能有筛子大小,高高低低的荷叶,铺满池塘,更有“田田”的味道儿。朵儿开的也大,开两天,老远能闻到阵阵清香,沁人心脾。每到乡下行走,路过荷塘,都会停下急匆的脚步,看上好一会儿。
父亲是庄稼人,喜欢种藕,年年不间断,为的是卖藕补贴家用。每年开春,父亲先把秧田犁了,留出二分地来,专种藕。
秧插毕,农事清闲下来,父亲就一门心思伺弄这二分藕塘,起埂,耙平,放水,得把塘好好泡一泡,直到泡软,泡稀,脚踩进去软软的才好。泡到是时候了,找出挖藕的工具,把年前留用的藕母刨出来,依次间空儿排到塘中的软泥里。
头道秧薅过,秧长到了一尺多高。塘里毫无动静,冷冷清清的一池静水,波澜不惊。父亲忙别的农事,不再管它。
蛙们成了塘的主人。灯火初上,影影绰绰,蛙声此起彼伏,声声入耳。很快,塘成了它们的产床,网状一样的黑仔,一缕一缕,或漂或沉。
天再热些,成群的小蝌蚪在塘里四处游走。终于,三三两两青钱大小的浮萍探出头来,歪歪斜斜,躺在水面,像刚睡醒的孩子,朦胧着双眼,这是长出的第一拨,总算见到荷叶了。
庄稼一枝花,全靠粪当家。荷喜肥,父亲伺弄起来自然上心,从不偷懒施施化肥应付,宁可费些力气,把一担一担的农家肥挑到塘里去。到坡地干活,也不忘割回一捆捆的青蒿倒进塘里,用脚踩进稀泥里沤一沤,增加池塘的肥力。
不经意间,塘里的荷叶渐渐多起来,东一块西一块地伸出水面。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,正是这时的荷。
阳历七月过后,碧绿滚圆的荷叶出落的亭亭玉立,有的高出水面二尺有余,层层叠叠的荷叶蓬蓬勃勃,挨挨挤挤,铺满整个池塘,“荷叶田田”就是这时的样子。
过些时日,花苞悄悄顶出水面,高过荷叶,含苞的,待放的,忽然之间,东一朵西一朵的次第开放,有的开出盘子大小。刚开时,嫩蕊凝珠,盈盈欲滴,微风过后,淡淡的、幽幽的清香四下飘散,路人经此,或驻足凝望,或沿埂行走,或放眼远眺,沉浸其中,不忍离去。
爱花是女人的天性,妻也不免俗,尤爱荷花。每到花开前后,总要赶回老家去赏荷。有时看得馋了,污泥也不顾了,脱了脚,下到半腰深的塘里折上几枝,回来放入花瓶,赏荷闻荷,只到花瓣尽落。
“万柄绿荷衰飒尽,雨中无可盖眠鸥。”有荣就有枯。几阵北风过,几经冷霜打,荷叶渐次衰败、枯萎,像犯错的孩子,耷拉着脑袋,在飒飒秋风中摇摆、颤抖。若会泼墨写生,此时入塘,必能画一幅上好的《残荷图》。
母亲对荷花似乎毫无兴趣,可能天天见,早已熟视无睹,印证了“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”的老话儿。不过,母亲倒是对干枯了的荷叶看得上眼,一一捡拾起来,扎成一捆一捆的,背回去晒干后垛在屋檐下。天冷了,背上两捆粉糠做猪饲料,在农人眼里,荷叶全身是宝。
该收的都收了,该种的都种了,也近了年关。河风吹得树梢呜呜做响,父亲找出钉耙、铁铲、小木铲,拉开大战藕塘的架式。铲开冰层,刨出深藏在乌黑稀泥里的粗壮莲藕。藕被分成四份,家里留一份,其余分给我们兄妹三人。如果收成好,父亲边刨边卖,换些油盐钱。自然,还要留上一小块不动,待来年做藕母用。
在乡下,能在水中盛开而清香不已的,恐怕就是荷花了。期待年年夏天,满塘田田的荷叶里,暗暗浮动阵阵花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