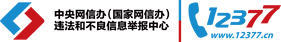婆娑舞姿和缥缈衣袂都落到身后,一首歌却飘入耳中,不依不饶:“家乡那棵红枣树,伴着我曾住过的老屋……”缠绵韵律和任妙音的柔声细腔一下子缠住脚步,化了内心对广场舞的固执排斥与抵触。心一颤,人回到故乡。
故乡的道场边,也有一棵红枣树。不,应是一排,立在场边的坎下,四五棵的样子,高大的形象,一如心中的父亲。儿时的我们,崇拜父亲。银白的月光下,父亲的故事像红枣树的影子和任妙音的歌声,缠绵心头。睡着了,还在梦里萦绕。
对红枣树的喜爱,无疑缘自树上的红枣。小时候的故乡,变化的只有春夏秋冬,不变的是对贫寒的固守。那些生长在小肚馋腹里的贪吃欲望,因为没有现在这样吃不完的糖果糕点填充,一开始就把目标移向那些能长果实的树木。红枣树只是其中一种,却一直鲜活在我记忆深处。
乡间的野果很多,差不多四季都有,三月黄、丫丫果、野桃子、剌莓、羊奶果、猕猴桃、野葡萄,火棘果……都时常在记忆里活跃。记忆有时候很奇怪,刚刚发生的事情记不住,少小喜爱的事物,却始终印象深刻。曾经有过的那些童年往事,不随年龄增加而模糊,反而刻画得更清楚,像风化在小纸盒里的红枣干,当年鲜红的光泽,至今还在闪烁。
故乡的红枣差不多在秋收时成熟,一棵棵挂在秋意阑珊的枝头,白里透红的风韵,像母亲当年的脸庞,妩媚俊俏,青春洋溢。
人们从四面围向稻场,稻场里是一座苞谷堆成的小山。这些白天从田里收回来的粮食,需要大家连夜撕去苞衣,剥成玉米棒子,等晒干后脱粒,按人口或劳力分给各家各户,差不多是一家人全年的口粮。说实话,我讨厌死了这种粗粮,天天吃,顿顿吃,胃口都吃倒了,还不止不休。讨厌的不止我一个,邻家小丫少五,村东的陈老头,还有张伯、银环她爹,都说过。可有啥办法呢?村里没水田。再说那年月,不饿肚子就算不错了,还奢望什么?
母亲和乡亲们围坐“小山”四周,朗朗的月光穿过稻场坎下高大的红枣树,漱漱地洒落在“小山”和那些飞快撕着苞衣的人们身上脸上,风一动,斑驳的树影像歌厅里的旋转灯光,打出交错的光影,忽明忽暗的映出他们的灰头土脸,劳累和快乐。大家手脚不闲,嘴也不闲,粗话俚语和荤段子一句句从男人们的嘴里不断蹦出来,像那些剥开的玉米,赤裸裸的,惹得小媳妇老嫂子一顿臭骂。不爱开玩笑或者被惹恼了的女人,有时也随手扔出手里的苞谷,恨恨地砸向说闲话的男人……山村金秋的夜晚,在男人的躲闪,女人的追打和一阵阵哄堂大笑中,海水般波澜。这就是他们的快乐。一天的劳累,都在说笑中舒缓,夜风里释放。
这样的夜晚很温馨,小村传统的集体农耕生活与人间温情,都在这些场景里淋漓尽致地展现,真实,动感,纯朴而自然。现在回过头去再找,怎么也寻不见。和家乡那些红枣树一样,不免引人怀念。
和大人一样,我们小孩也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,玩耍之余,人多胆肥,趁着大人们忙着撕苞谷,偷枣。那时枣属于集体,平时看管得很紧,任何人不能随意采摘,小孩也不例外。看着树上红得诱人的枣,胆大顽皮的孩子借着大人们的哄闹作掩护,抱起早就准备好的大石块轻轻撞向枣树,“咚——”一声闷响之后,枣“扑扑扑——”落了一地,我们却蹲在树下,大气都不敢出一口,生怕刚才的声音,惊动了稻场里欢声笑语的大人,偷枣不成,反引来祸害,直到感觉安全了,才借着透叶而下的月色,摸索起地上的枣,来不及擦洗,就丢进嘴里,嘎嘣一声,香甜清脆就囫囵着咽下。偷枣不可能有公平分配,比的是眼尖手快,谁抢的多,谁就多吃几颗。倒是那种偷枣的忐忑,心跳的剌激,偷吃的香甜与畅快,让枣在记忆中刻下了不灭的儿时情趣,生出一世依恋。
多年以后,我远离了家乡,如任妙音所唱:“当初离开家的时候,枣树花香开满枝头”。可在外面走了一圈之后再回到家乡,那些儿时无比爱恋的红枣树,却已不见了影踪。一同不见的,还有堆苞谷的稻场,稻场旁的土屋,土屋后面我读过的村小,以及村小下面放着两只石碾的小操场……那些,都是我儿时最美的记忆,它们消失得我心痛,仿佛再也找不回过去的故乡。
“红枣树,家乡的红枣树,儿时我爱过的恋人,现在你身在何处……”任妙音的歌声依然缠绵缥缈,入耳清晰,颤动心神,仿佛那棵红枣树,长在心里,从不曾消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