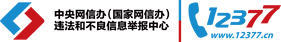七月桃
我们上学那会儿,没人专门栽果树,一棵挨一棵连成片的果树林更少,能看到几棵果树,无非是房前屋后或田边地角自然长出来的,孑然独立,自成风景。这已经很不错了,能长成这样,幸亏不防碍田地里的庄稼,如果碍事儿,就被砍了当柴火烧了。那个年代,一切得给庄稼让路——粮为贵,其它均为轻。
夏日炎炎,除了背着大人偷偷遛到河里洗澡凉快凉快,我们最喜欢耍的地方,在一处密林里。这个林子里,鸟雀多,尤其画眉多,我们自制了木弹弓,常到林子里打画眉,之所以打它,似乎并不为什么,只是觉得追着打它好玩儿罢了,顺便检验一下自己瞄准度高不高,偶有收获,乐不可支。这片林子,绵延有近半里路,林大幽深,凉爽异常。林下有一井,用方方正正的石条层层垒成的,四角分明,严丝合缝,显然是石匠专门打的石条,足见有些年份了。井水夏天清凉,而冬天又冒一股股的白烟,真正的冬暖夏凉。挨着井旁,斜着身子长出一棵桃树。桃树不大,长得有些勉强,估计是竹林遮阴,长期遮挡了阳光的缘故,限制了桃树的生长。树虽不大,但结得果子不少。这是一棵七月桃,个大,果子快熟时,我们每天都去看看,有时,一天去好几遍,到井旁耍耍,抬头瞅瞅,惦记着桃子熟了没有。
这棵桃树似乎没有归属,有点公家的意思,所以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常围着它转,打它的主意,却无人干涉,这越发滋长了我们偷吃的野心。
看到画眉在啄桃子了,我们知道桃子能吃了。摘桃,并不需要上树,虽然我们个子都不高,但站在树下,伸手就能摘到。熟了的桃子,可以轻松地用手掰开,一掰两瓣,嘴里吃一半,手里拿一半,慢慢享用,这样的暑假真是有意思。
通常,把桃子摘下后,我们并不急于吃掉,相互攀比一下大小、好坏(有些桃子长虫,看相不好),然后统统丢到井水里,让它冰一冰。桃子落水后,很少有沉底的,大多漂浮着,晃荡着,已分不清哪个是谁摘得了。待冰得差不多了,弯下腰,就着井水,把桃洗干净,这时再吃,又凉又甜,又脆又爽。这棵桃树上桃子的味道,给我的印象极深。后来,吃过不少地方的桃子,都没有这般滋味儿悠长。
吃过桃子后,桃子核我们并不乱丢,都收藏着,攒多了,用铁锤把它们一一砸开,放到竹席上,晒干了,一口袋背到供销社去,得了钱,买几本小人书回来,猫在阴凉处,一页一页地翻看,别提有多快活了。这样的暑假,现在的孩子怕是没有享受过。
八月枣
我们那时的暑假,只有几本人教版薄薄的语、数、外主课作业,都不超过50页,如果肯下点功夫,三五天可以全部做完。但我们都不急于做,领到手后,写上姓名、班级,放入书包,自此几乎从不翻动,直到临近快开学了,才想起来,翻拣出来,心急火燎地做一做,对错都无关紧要,只要不留空白,基本不会挨批。那时根本不兴补课,暑假以玩为主,以帮家长做农活、干家务为主。
我每年的暑期,都以放牛为主。还是生产队时,我们家与伯父家合伙分了一头牛,这头牛,两家共有,轮流放。一到暑假,轮到我们。暑期正是高温期,放牛需要起早,天不亮就得把牛赶上山。我对放牛并无兴趣,但借放牛起早之机偷别人家的枣子,还是挺兴奋。
我们自己原来有几棵枣树,长在地边,有点儿息地,父亲种地时,屡屡挖它伸进地里的根须,这样一来,虽然树还活着,但并不旺相,病怏怏的样子,树上的枣子,总是稀稀拉拉,零零落落。我们放牛要经过的这家,枣树长在园子旁,有十几棵,每年夏天,枣子都长得喜人,满树的枣子挂在枝头,压得树枝垂的很低,这越发为我们偷枣提供了便利。
从枣子半熟开始,我们就下手了。每次从树下经过,天还没大亮,这家的主人估计也没起床。我们伸手,先把低处的枣子收拾了,并不一颗颗地去摘,那样太耽误工夫,作贼总是心虚,总想速战速决,总会动作麻利些,所以,我们每次偷枣,实际上是用手去撸,这样,能把一根枝条上的所有枣子都撸不来,管它大小,熟的,没熟的,都装进衣兜里。枣树枝条上有刺,这算什么呢,忙乱中顾不了那么多。撸不来的枣子,连同枣树叶子一起带走。
主人家看低处的枣子越来越少,是否叫骂过,我们并没听见,或许叫骂过,只不过我们在山顶上放牛,听不到而已。他们找来竹杆或细长的树杆把低垂的枣树枝子支撑起来,这样,枣子高高挂起,没有工具,根本摘不到。这有什么难?!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,有的是办法,正是“坏”得要命的年龄,正好借他的杆子打枣。每次都有分工,一人放哨,一人敲打,剩下的在地下捡。一会儿工夫,小半树枣子都落到我们口袋里了。
没熟的枣子,我们也敢吃,那时好像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,胃口好的很。有时,这种没熟的枣子吃了会拉肚子,但这并没影响我们偷枣的热情。
一晃,三十多年过去了,但我仍然怀念那段偷枣的艰难岁月,它是童年一段青涩的记忆。
磨核桃
“稻谷上床,核桃满瓤。”这是乡下俗语,意为核桃长熟,要到稻谷收割以后。所谓“稻谷上床”,指的是稻谷草铺上床,物质贫乏年代,乡下人都用稻谷草铺床,这种东西,既易得,又暖和,几乎家家如此。
长在门口的一棵核桃树,至少有一百多年了,树上有无数的疤痕,这是每年过年时,以给它喂饭的形式用刀砍下的,当初的伤口虽已愈合,但疤痕还是无情地留了下来,就像身上的疤痕一样。核桃树下,是我们的乐园之一,很多美好的童年时光都是在核桃树下度过的。
核桃还是青皮时,我们已经在动它的心思了,我们并不完全相信“稻谷上床,核桃满瓤。”这句话,因为稻谷上床时,暑假早就结束了,收核桃已经是大人们的事了,与我们几乎无关了。我们希望的是:收获要与我们有关,所以,很多时候,我们提前动手,去试一试,核桃是否能吃了。
我们动用很多办法让核桃从树上掉落下来,上树摘,站在地上用石头瞄准了打,用长棍子敲,这些滚落下来的青皮核桃壳子很难分离,毕竟没有成熟。而不去掉青皮,是无法吃到里面核桃的。去皮,这怎么能难到一群好吃的孩子呢。我们把核桃皮放到外形粗糙的石头上磨,翻来覆去的磨,直到把所有的青皮磨干净,当然,手上会沾上一层青皮的粘液,这种粘液很难洗掉,能在手上留半个月左右的时间。磨去青皮后,我们把核桃放到水里洗一洗,核桃的轮廓完全出来了。敲开,就能吃到核桃瓤,还没完全长好的核桃有一股水腥气,并不怎么好吃。磨出来的核桃,我们大多作为放在手里的把件儿,反复搓玩,有点像现在搞文玩的那些人。如此看,我们是最早的一群文玩的孩子了。当然,核桃最后的命运,就像猫子逮住老鼠后,并不急于吃掉一样,直到玩得差不多了,才吃。我们也一样,核桃玩够了,还是用石头或锤子砸开,有时也放到门缝上挤,破开后,吃掉,尽管味道并不如完全成熟后的核桃好吃,但毕竟是吃食之一呀。那个年代,有,总比没有强。
浸柿子
直到我们快上学时,柿子也没长好。我们那里产两种形状的柿子,一种锥形的,像砌墙用的吊锤,蒂处浑圆,顶端却尖溜溜的。还有一种,扁圆形,这种最为普遍,大人们称之谓“保康柿子”,我们是保康县,以地名命名一种果实,以我的印象,绝无仅有,这也足见保康柿子之多。这些青皮柿子在我们刚放暑假时,只有乒乓球大小,两个多月的时间里,也只长到拳头大小,浑身青皮,一看就知道还是涩的,根本吃不了。但孩子们是不甘心的——想办法浸了吃。
柿子除涩味儿,有一种植物是天然原料——蓼子,它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,能长到半人高,一丛一丛的,亦称“水蓼”。叶披针形,花小,白色或浅红色,果实卵形、扁平,叶片细窄,揪一匹放在嘴里嚼嚼,有一股辛辣味儿。蓼子一点也不难找,河滩上,水沟旁,稍有水的地方,随手可得,大人们常用它们的红籽作酿酒的曲子用。
把青柿子摘一些下来,不能碰破,拎回家。找一个罐子或坛子出来,大小以能装下几十个柿子为好,太小了,泡不了几个,讨一场力不划算。我们每次浸,最小也要浸三十个以上。把柿子一一放到罐子或坛子里,烧一锅开水,烧开后待凉,凉好后将冷开水倒进罐子或坛子里,封严即可。在封坛口时,我们有时会学大人泡菜的法子,取一些干苞谷叶子堵在坛口,确保所有柿子都能浸在冷开水中。找一块薄膜,蒙在坛口上,用细绳在坛口下的“颈脖”处,反复围着缠几圈,系紧,如此,真是密不透风了。一个星期左右,浸好的柿子即可食用了。
还有一种方法浸柿子,比这个更简便。把摘下来的柿子用衣服兜了,走到稻田边,稻子长得正欢,脱脚,人下到田里,把柿子依次按到稀泥里,使其浸泡,这种浸法,真是方便。不过,为防浸好后不易找到浸柿子的地方,我们会在按柿子入泥的地方插上一根树棍,算是作记号。柿子浸下后,我们每天数着日子,看还有几天可以吃柿子了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,按棍索骥,将浸好的柿子一一请出来,去皮,味道并不比秋天的红柿子味道儿逊色。果子没有真正成熟,通过人为干预,提前吃到果实,而且味道是另一番滋味儿,除了柿子,我还没有见过第二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