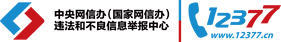一
“在悠长而严肃的永生中,谁不忘记自己的童年,他就是一个诗人。”
——巴乌托夫斯基(俄罗斯)
当然,一切要从老家说起。
通常来讲,老家是一个人的祖籍所在地。我的老家就是父亲的出生地。那是一个沮水河边的小镇。对我而言,它是一条陌生的水域,因为我从没有亲近过它。可是对于父亲,却是他生命里极其重要的一条河流,因为它承载了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。从父亲对他年少时期极简短的描述中,我可以捕捉到这条河流的一些浮光掠影。那条河,大概也是极美的。两岸树木丰茂,灌木低垂,河滩洁净,白色的鹅卵石是捡也捡不完的珍珠,大块的巨石是可安睡入梦的小床。父亲成天在河里扑腾,河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不会凫水的。那应该是他童年的乐园。这条河离家不过是走过一段田埂,再横穿一条街的距离。
老家的旧事最早在出现在我少时懵懂的眼睛和耳朵里。
十八岁以前,每年过年都是要随父母回老家的。关于过年的模糊印象可以追溯到五六岁甚或更早。老家有一座俗称“明三暗六”的大瓦房,房前有树有田,房后背倚青山,红砖黛瓦的房屋座落于此更显气度不凡。院中有花园鸡舍,果树繁茂草木纷批;屋侧有田,多种薯类;屋后有沟,干净齐整。我记忆中的老家永远是这样的一派田园风光。暮春傍晚,搬一把旧木椅坐院里,从身后吹过来一阵风,飘荡着马铃薯花的芬芳。回首一看,马铃薯秧苗在晚风里荡漾成一片绿海,海浪上白帆点点——那是密密簇簇的马铃薯花随风在摇曳。我眼中这么美丽的老家,是父辈们用汗水和心血绘就的。
老家,曾是一片废墟,是一片空荡荡的荒地。从父亲口中得知,盖这所房子的时候,他已“下放”,作为知青。从母亲多次差不多要声泪俱下的“控诉”中,我也知道搬进新居时已有了我和妹妹。时值寒冬腊月,因为新房子仅仅才盖了瓦而尚未隔上天花板,只用油布在梁上蒙了一下,风从瓦隙间肆虐而入,一家人缩在被子里冷得直打哆嗦。父亲忙着搭梯子去扯弄被风卷皱的油布,以堵住无孔不入的冷风;母亲则把两个孩子焐在臂弯里,孵小鸡一样,把自己的体温传给我和妹妹。正忙活着,只听爷爷在那屋一声咆哮:有这样住的就不错了!折腾什么呢!父亲停下,轻手轻脚下了梯子,和母亲相觑无言。世界瞬间安静了。只有风过如狼吼。
噢,爷爷,我父亲的父亲。从来就是疾言厉色的一家之主。儿孙们在他面前从来就是噤若寒蝉。他永远有做不完的活,却从来没有说不完的话。我并不责怪爷爷,在读了这么多的书经了这么多的事以后,我想,一定是太多太多的苦和难把语言这样一个泄漏感情的门给他堵上了。他只有不停,不停地用双手劳作;不停,不停地率领家人们劳作;他不停地淌下汗水,才能不停地堵住停滞在胸口的泪水。我的父亲,拥有这样一位勤劳苛刻的父亲——他生于湘西,长于湘西,正值青年被抓作壮丁,中途与队伍失散,流落至现在老家附近的一条小山沟,特殊年代里受尽白眼,中年又丧失爱妻……从小,我就发现爷爷奶奶的卧房里挂着一张女人的画像,也记不清是谁偷偷告诉我,那是我的亲奶奶。
现在不得不说的事走向幕前。父亲幼年丧母。
那时父亲4岁,叔叔年仅2岁。奶奶在26岁的芳龄逝去。生活给了爷爷怎样的赐予?又为何如此残忍地将之夺去?那墙上悬挂的画像似能告诉我些什么,却又让年幼的我一次次感到莫测的神秘。我常一个人趁大人不在偷偷站在墙角下仰望,那是一幅素描,笔法简洁,却细致入微。衣衫还染了色,是紫红色,酷似夏日田野的紫苏,有一点娇艳和几分嫣然,衬托着奶奶的面容上那一抹宁静安然的笑容。
那笑容静止在26岁的灿烂年华里,既有青春的飞扬,又有母性的安祥,当是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。所以,那笑容也静止在爷爷的心窝里,一辈子也不会飞走,不会弥散。
直到现在,当我已为人母,有了孩子在身边翩然,才更能体味那样一种情境——我不能想像一个小孩子,突然失去了朝夕庇护他的那个人!而父亲就是这样,在懵懂无忧的年纪,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光突然被无情剥夺。当然,更痛苦的人是他的父亲。他作为儿子,最大的任务是成长,而爷爷却还要将人生继续,即便在苦水里泡着,也要把儿子们养大。
……
爷爷一定是更缄默了,一幅画像伴永生,就算以后再立新家。爷爷一定是更勤劳了,男儿用汗水替代泪水,流进土地,流进手下的每一件活计。爷爷一定是更苛刻了,对待儿子们是疾言是暴语,是内心深藏却无法表露的心痛与柔情。父亲也得接受这一切,没有了如日月生辉般的母慈,父爱也因谋生的艰难更似于头上的雷霆。他有一个怎样童年呢和少年呢?在他十六岁“下放”以前,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?
我曾因好奇父亲眉毛上的一条杠向他打听过他的童年,而只得出他儿时无比顽劣倔强的结论,并屡次取笑于他。而他大概也因自己童年父爱的缺失,对我和妹妹自小骄宠,反而有时放下了身为父亲的尊贵。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,我不能眠,突然想起“父亲”这个词汇。多么多么高大上的名词啊!我深省着他作为父,我作为女的许多行为,在心中深深惭愧了。那一刻,我想起父亲偶尔在餐桌上提起他小时候得到的他外婆的宠爱,他总是这样起头:一放寒假,我就到尤家河去了,我婆婆,也就是你太太,给我留了油条,说这是给平儿(父亲乳名)留的,谁都不准吃!父亲讲起这些,也许是餐桌上遇见了他在外婆家吃过的东西,勾起他不多却深刻的童年回忆。当他说着的时候,一向冷肃的表情和眼神都变了,虽不至于有泪花在闪烁,脸上却突现了一个平日里少见的,名叫“柔和”的词语。而我,只是忽忙地扒拉我的饭菜,顾不上听他仔细怀旧,依旧用戏谑或者嘲弄的口气一笑而过。
我似乎,就没用心去听父亲讲那过去的事情?我那纷杂的心,似乎就从未在父亲那凄然的身世中多作停留?
是父亲,一生刚强,如一棵大树撑起一片屋脊,我却不知道树使出的力气;是父亲,沉默多于温柔,我便不去探究那沉默的背后是否涌动着一条湍急的河流。
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得到的爱,足可以温暖他的一生。父亲念念不忘的不是他的出生地——老家,而是一个名叫尤家河的小山村。那是他母亲的娘家,有给他留好吃东西的外婆。我只是好奇地问过他:“尤家河”有河没?父亲答:当然有。可是言辞不多文采不深的他到底也无法向我描述出尤家河的风光,只是从他那略略几句“小河里逮鱼”、“树上掏鸟窝”的袖珍版回忆里,我可以展开一些关于秀丽山村尤家河的想象。
什么会长驻在一个人永生的记忆里?
父亲在老家完成了他童年和少年的成长。在这段岁月里,孤寂、苦闷和灰暗一定是主色调,尽管也有一条名叫“沮水”的河流放逐着欢乐,可我知道,唯有小山村尤家河的那条无名小河脉脉流淌着缕缕温情。
老家,在父亲十六岁的时候,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。
二
“没有故乡就没有诗人。”
——叶赛宁(俄罗斯)
现在要说到故乡这个字眼。因为父亲的脚步已经从老家出发,走向了这个被我称作故乡的地方。
我一直认为,那是他的第二故乡,因为他在那里收获了爱情。那儿也是我的故乡,因为我是他赋予的新生命,在河岸边的小镇诞生、成长。
那年父亲16岁。因为家里从商,是“商品粮”户口,便在初中没有读完的时候,作为“知青”下放。他背上背着被包卷,带着干粮,徒步三十公里翻山越岭来到了另一条大河边上。从此,他与这条河流结缘。这条河,一定是流动着父亲灿然的青春。
这是一条怎样的河?无需回忆,我闭上眼睛,便可看见它的模样。它的名字很好听,粉清河,比“沮水”更生动形象,更旖旎生姿。多年来,我总是怀念着它,虽然弄不清楚它的源头和走向,可是它的波澜壮阔,它沿岸的丰饶景象似一幅宏美的画卷,随时会打开铺展在眼前。有时,我暗自比较,沮水流经的小镇,两岸树木葱郁,水草丰茂,一派恬然,有些小家碧玉似的江南水乡的影子。横穿小镇的粉清河,则以气势惊人,两岸崇山峻岭间,夹着万亩良田,稻花绵延百里;辽远的河滩望不见对岸,幽深的河水逶迤东去,绕着青山走向天边。我短浅的目光追随着它,却看不见它的来路,也看不见它的去向——站在高高的山头,我只能看见绿幽幽的粉清河匍匐在对岸的青山脚下,化作了碧绿的玉潭,三十年不变,也亘古不变。
话说回来。父亲初到这条河边,一定十分惊诧。白花花的河滩,烈日下白得耀眼,这不是一条温柔的河流。它暴烈,在雨后经常涨潮;它咆哮,浪花浑浊发出震天世吼;它平静时幽深,却暗藏漩涡,仿佛水底有怪兽张着巨大的嘴巴;它暴涨后浩浩汤汤,像江洪急切地要奔流入海。这不是山平水缓的老家,这是一个想以如此声势唬住一个外来年青人的陌生地方。一个山高水急的穷乡僻壤呈现在父亲面前。
当年这个小镇困苦得像步入了穷途末路,可那波澜壮阔的水域和高耸入云的大山里却隐藏着深不可测的能量,就像一个人身上蕴藏着无穷潜力,需要去一点点挖掘。父亲无疑是这样的人。关于父亲插队、招工的经历,我并不甚详,但我知道,这一程真正步入农村的集体生活,对他自幼顽劣倔强的性格是一次历炼。我看见过父亲那一时期的照片,典型的“愣头青”的样子。头发很短,往上竖,眉目有神,嘴唇敦厚。整个脸庞被一种清朗刚毅的线条勾勒,算得上英气逼人,堪称风华正茂。我知道他的第一份工作是供销社门市部售货员,给人称白糖,灌醋打酱油,拨弄算盘珠子。以爷爷严格的家训教育出的儿子做起事来当然是最棒的。所以没两年父亲就“高升”为供销社统计员,又年纪轻轻当上了供销社负责人。那时,他才26岁。在这个临水而居的小镇上,恍然间他已闯荡了十年。
那时,我出生了。
一个生性敏感的孩子总是对父亲母亲的年轻往事充满了探究的兴趣。哪怕是一双还听不甚分明世事的耳朵无意捕捉的字眼,哪怕是在抽屉里翻弄出一张发黄的信笺上模糊的笔迹,哪怕是相册里一张张黑白老照片隐隐透露的故事,我都一样保持着敏锐的嗅觉。所以,无论是老家的旧事,还是那段在故乡生活了十年的日子,我早已在记忆里把它们串起来,串珠子一般连成了一根散发着水晶般光泽的链子。妹妹们与我兴趣不同,她们都保持着宁静的心,或探索学术,或醉心于寻常日子,而我是个怪人,几十年把一份记忆翻过去嚼过来,从中咂摸着属于自己的种种滋味。
关于父母亲的相识,我并没有听过他们详尽的讲述。我只是从母亲偶尔戏谑父亲的小片断里去放飞想象。凭着对故乡这个美丽小镇的无穷好感,我自然也在想象中赋予他们的恋爱经历无穷的浪漫美感。事实上在那个年代,一切与浪漫无关。我只是觉得父亲敦厚诚实,虽然寡言,但一身英气;母亲自然是真善美的化身,两条大辫子,脸庞圆润,身材高挑俊美,整个人神采奕奕。更重要的是,20出头的母亲不仅是根正苗红的农家女儿,并且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,带领孩子们勤工俭学的优秀事迹一度在广播里传遍了粉清河上下。直到有一天,母亲的名字又飘至了沮水沿岸,传进了爷爷的耳朵,一辈子尊师重教的老人家逢人便夸他这能干的儿媳。这是后话。
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神话,我相信。父亲和母亲,一个生长于沮水边的小镇,一个在粉清河西岸的小山村长大。他们的相遇,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说偶然却又必然的缘分。两条不同的河本不会交汇,却一路奔腾终入长江。父亲母亲本不会相识,却从不同的方向奔赴对方,牵手一生。我曾在母亲偶尔抛洒的点滴话头里想像一些情景:在母亲执教的窗外,有从插队点赶来等候的父亲。他没有什么多的话说,只是站在校园里的大柳树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下课铃响了,暮色也渐渐笼起,烟灰色的黄昏里,大河小河若一宽一细两条银练,沿着小镇环绕,他俩一定也是用轻慢的脚步和轻快的心情把小镇一步步环绕……这便是我能做出的最最浪漫的想象,关于父母爱情。
只是生活不可能是浪漫诗意的想象。在我心中,贫穷艰难是永远铭刻的记忆。母亲因为过于劳累,也因为自然环境极其艰苦,少时羸弱的身体不堪重负,在气候变幻如四季瞬息的高山里淋了一场雨后,招致事关神经的大病。父亲那时事业渐起,四处奔波,天南海北,家里母亲又是工作又是年幼的两个小女,还有时好时发的病痛。有时,我情愿在记忆里抹去这一段,可是不能够,因为它已经那么深那么深地镌刻下来。
故乡!短短十载的日子,为什么令人终生回望?那是我初来人世的一程,所有的经历都是新鲜的,所有的景物都是世界在我眼里的第一次投放,所有给我爱的人都留在了今生不灭的记忆里。细想来甚至有一些感激命运,是它安排了父亲远道而来认识了母亲,而把我留了在这珍贵的人间。
故乡是父母亲与我共同的家园。有它,足可以温暖一生。
记得有人说过,故乡不只是一个存在,而是想到它时有一种辽阔的心情。这心情,是辽阔的淡忘,也是辽阔的不舍。数年前坐车离开小镇,车拐过一个大弯,老屋门前那座酷似驼峰的“双牛尖山”突然就不见了,我回过头一下子流下泪来。就像今天,写下这些,又流下了久违的泪水。
保康微信平台 微信号:baokang0710 编辑:张满玉